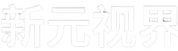2025年,一组数据引发社会热议:全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突破15%,而16-24岁青年失业率仍达14.2%。在这一背景下,“全职儿女”群体迅速崛起——他们选择暂时脱离职场,回归家庭照顾父母,通过承担家务、陪伴就医等方式换取经济支持。这一现象被部分人视为“新型尽孝”,也有人质疑其本质是“啃老”的华丽变装。

尽孝视角:家庭责任与情感回馈
支持者认为,“全职儿女”是传统孝道的现代实践。例如,宁波李昊辞去上海高薪工作,专职照顾患病的母亲,每日做饭、打扫、陪诊,甚至通过炒股、学习维持个人成长。这种选择不仅缓解了父母的孤独感,更在快节奏社会中重建了代际情感联结。社会学研究指出,老龄化加剧下,家庭成为养老核心载体,子女通过“全职”角色弥补社会养老服务的不足,实质是家庭韧性的体现。
啃老质疑:经济依赖与个人发展停滞
反对声音则聚焦经济依赖与职业空窗期风险。部分案例显示,一些青年以“考公”“考研”为名长期居家,实则逃避就业压力。如某“海归”硕士回国后连续两年未稳定就业,依赖父母“工资”生活,虽承担家务,却因缺乏职业规划被亲友视为“变相啃老”。经济学家警告,若缺乏技能提升或过渡计划,“全职儿女”可能滑向“终身依赖”,加剧家庭经济负担。
社会背景:就业压力与代际价值观碰撞
现象背后是多重社会矛盾的投射。2025年高校毕业生达1200万,就业竞争白热化,许多青年选择“慢就业”作为缓冲。同时,Z世代更重视工作与生活平衡,抵触“996”模式,短视频、自媒体等新业态也提供了居家创业可能。然而,这种选择在传统观念中仍存争议——父母辈往往将“独立”视为成年标志,而子女则试图在孝道与自我实现间寻找平衡。
破局之道:政策支持与个体能动性
专家建议,解决争议需多方协同:政府应扩大“青年见习计划”覆盖范围,提供职业培训补贴;企业可试点“灵活用工”模式,吸引暂时居家青年参与兼职;家庭则需建立“过渡期”规则,如约定技能学习目标或社会贡献时长。正如学者何雨所言,“全职儿女”本质是“社会避险机制”,其可持续性取决于个体能否将家庭支持转化为职业跃迁的跳板。
当夕阳洒进厨房,宁波李昊正为母亲准备晚餐,而几公里外,他的简历已通过某在线教育平台的兼职审核——这或许正是“全职儿女”的最优解:以家庭为港湾,但航向始终是社会的大海。
版权声明
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,不代表百度立场。
本文系作者授权百度百家发表,未经许可,不得转载。